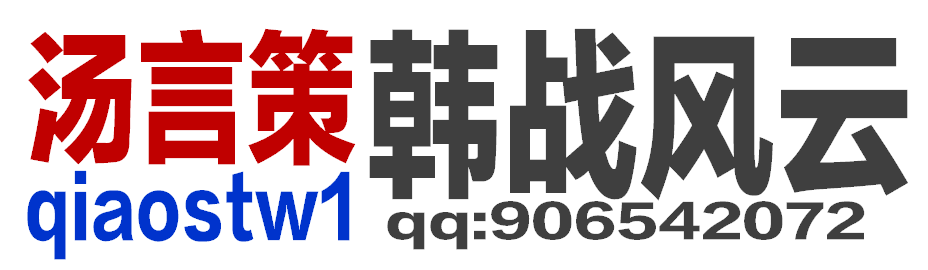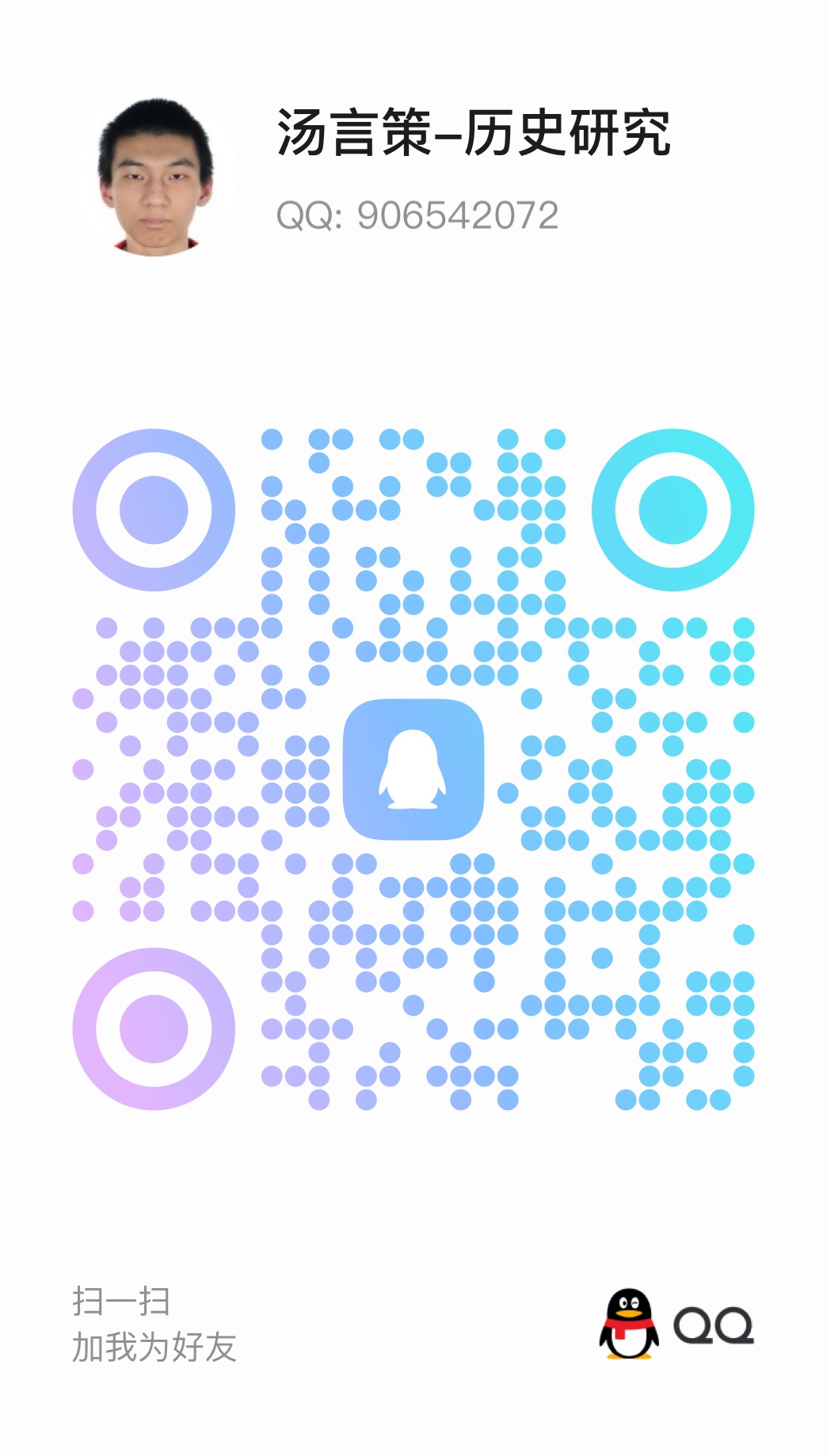袁殊和潘汉年的“亲日性质”有本质不同
1955年,潘汉年和袁殊先后被逮捕、隔离审查。
当时袁殊已经改名为“曾达斋”十年之久,但仍不能躲过这场清算。
从此,二人余下的人生,基本失去自由。
潘汉年直到1977年离开人世,仍然背负叛徒骂名。
袁殊幸运一点:1982年他活着看到了自己的“平反”文件。在人生余下的5年时光,他丝毫不为自己当年的选择有一丝悔意。但据说袁殊离世前,精神已经错乱①。
如果还原历史,我们不幸的发现:袁殊的“亲日反民族”帽子,并不是很容易摘掉。
首先,他是“汪伪政权”的“清乡工作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”,直接参与过对抗日武装和文化团体的镇压。
袁氏由于在汪伪“文化战线”的“业绩”出色,后来还担任伪上海市教育厅长、市政府参议,更担任过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这样的“狠角色”。
袁殊以上的经历,坐实了他即使不是“直接”投敌行为、也是“间接”投敌行为。“亲日”这顶帽子不好摘,功过实在难抵。
假设按照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的标准:袁氏既当过伪政权“爪牙”、又镇压过抗日人士(有证据显示他参与过对沦陷区亲重庆记者的迫害),是妥妥的“亲日反民族分子”。
袁殊怎么想的并不重要:汉奸论迹不论心。现代法律也明确要求:看人是否犯罪是要看他做了什么、产生了什么后果,而不是看他有什么“初衷”。
建国之后,了解袁殊的人,对袁殊人品表示不屑的大有人在。
据说聂绀弩在北京遇见过袁殊(已改名曾达斋),当时袁穿着解放军制服,热情地向聂打招呼,却换来聂一句嘲讽“你又穿上这身衣服了?”(没有找到原文出处,是否是坊间传言不得而知)。
但是袁殊在沦陷区“下水”的经历,当年在上海文艺界可不是一件小事。③
潘汉年的“亲日”性质则与袁殊颇为不同。
建国后潘汉年被逮捕后,对他最严厉的指控、乃至于一系列罪名的导火线,是潘汉年经大汉奸李士群牵线,与汪精卫有秘密会面。
但潘是奉命行事,性质上与袁殊有本质不同。
潘汉年住进李士群的家,与日本外务省驻上海的代表岩井英一有过几次秘密接触,并且通过他的引荐见过日军中国派遣军副司令影佐帧昭(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),讨论过“互不侵犯”和“合作”问题,还面见了汪精卫一次。④
日本政权派系林立:其外务部门和军方,历来互不隶属更互不买账。潘汉年的活动主要是跟外务部门对接,与日本军方沟通不多。
在战争背景下,这样的沟通显然并不能取得什么效果。
至少从公开资料来看,并不能说双方达成了某种协议,充其量是某种默契而已。
但是这些秘密会见,日后都给背锅的潘汉年惹来了不小的麻烦。
一言以蔽之,潘汉年和袁殊建国后被整肃,原因无外乎“亲日”二字。但袁氏是“半推半就”、潘氏则是代表组织行为,因此我认为:潘汉年案才是地地道道的“冤案”。
潘汉年在1955年由于这段历史被“留置审查”,直到1963年才定罪,期间由于“改造态度良好”,潘氏虽被囚禁、但生活待遇不差。
直到1966年。
其实细想起来,潘身陷囹圄但仍受优待,其中原因很简单:潘汉年与日本外交界和汪伪的秘密联系,都是奉上级的命令,潘汉年只是一名执行者而已。办案人员乃至于最高层、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。都是专政机构、难免生出兔死狐悲,手下留情可以理解。
1982年潘汉年和袁殊同时被平反。
潘是地地道道的沉冤昭雪,袁氏只是沾了“改革春风吹进门”的光而已。
可见中国当代历史上,“亲日”还是“不亲日”,压根根本没人在乎过。汉奸不汉奸的、要看情况再定。
大家只是大目标下的小棋子。
而且真亲日的,也不仅仅只有一个小小的潘汉年。
① 《辽沈晚报》2009年4月23日第8版《中国情报史上的“多面”袁殊》
② 灰色地带”中的挣扎——“孤岛”与沦陷时期(1937—1945)上海文化人的行为分析-葛涛
③ 同上